
毕亮,八十年代生于安徽桐城,2004年到新疆,现居伊犁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新疆作家协会理事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站在魔鬼城的阳光下,我对一切解说置若罔闻。我深陷其中,时间的痕迹遍布……地貌、风沙、过往的人流。
在有限的时间年代里,红柳荣枯都有迹可循,一年下过的几场细雨,也都有专人记录。可是,时间的轨迹让人捉摸不透。但此刻,炙热阳光下,地面上的烘烤,让立在其中的人,就像是草原上平锅里的肉,上和下都被文火烤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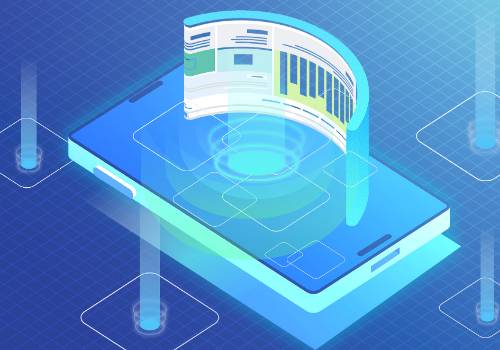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走动或停步不前,时间和汗水一起在皮肤上流下了肉眼可见的轨迹。有汗水滴落进细沙,瞬间被隐去,如一滴水撒在伊犁河、一滴雨落在赛里木湖,无可寻觅。几滴渗进沙粒里的汗,也许是我留在魔鬼城唯一的痕迹?即便已经看不见,我已来过,被这里微乎其微的风吹过,被阳光直射地晒过。为了不虚此行,我是不是应该从魔鬼城带一些什么回去?(会不会不道德?)
想也不想,便蹲身捡起脚下的两块石头,烫手,却忍着没有扔出去。从石头上,我看到了时间的磨难。石头在黄沙中,黄沙在魔鬼城,魔鬼城在乌尔禾,乌尔禾在克拉玛依,克拉玛依在更阔大的戈壁中。长河落日圆,是一种时间的描绘,而大漠孤烟直是一种人生际遇。时间之下,人的际遇如黄沙,吹往不同的方向,如来往的人群,流向不同的远方。
在魔鬼城的沙地里,我捡了两块石头准备带回伊犁。这是时间让魔鬼城给予我的馈赠。在回伊犁之前,我要先在乌尔禾住一夜。
乌尔禾的黄昏,一阵急雨打落暑气。打落的不仅是乌尔禾的暑气,更浇灭了残留在体内的魔鬼城的热。一场雨之后,身体开始变得凉爽。带回来的石头,经雨淋过,更显圆润,真的不虚此行了。
有风吹过乌尔禾的时间里,我早晚绕着住处的建筑群散步。平地而起的楼栋,是现代人的时间。站在一棵桑葚正青的树下,我消化着昨天百里油田的奔波。
百里油田的绵延百里,是时间的足迹。每一口井往地底深处,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,时间以石油的方式在行走。时间的血脉在茫茫戈壁是流动的传奇,是时光之子给与人类的福祉。
行到路尽处,坐看磕头机。磕头机,以此来命名采油机,是石油人对时间的感恩,对大自然的感激?我没有问当地的朋友,甚至没有和同行人交流,一路触目所及,采油机都在一边“磕头”一边抽油。
我还没有走到路尽头,就停在了风城油田。在这里,我得以近距离仰望磕头机,并贸然地和它们合了张影,以照片的方式留住了磕头机和我的时间。
但张玉华的时间没有留住。张玉华是风城油田采油二站“张玉华班”的班长。这个以她名字命名的班组,清一色的巾帼英雄,张玉华是当之无愧的“领头凤凰”。她这只“凤凰”在十多年的时间里,走在技术革新的探索前沿,带着她的班组,走上了一个又一个领奖台。柜子里的一个个奖杯奖牌,是流动的石油,更是凝固了的张玉华的时间。一个女人的青春,一群女人的青春,就在油井与油井之间奔走。而1973年出生的她,明年即将退休。
张玉华的时间大事记里,需要记录下1992年。这一年,十九岁中专毕业的她,走进油田成了一名石油女工,一待就是三十年。属于她的时间是从1992年开始的,张玉华和她的班组的时间,是基层石油女工的青春,是献给石油事业的日复一日,不是壮举,却不可或缺,无可替代。张玉华们认为,她们都只是一名基层石油女工而已。
在风城油田采油二站,和张玉华班组隔磕头机相望的是李荣辉的国防班组。这个由二十二名转业军人组成的采油四班,每名采油工人都保持着“退伍不褪色,退役不退志”的本色,从他们平时的走路姿势、内务整理……走在采油四班如入军营。
李荣辉不是国防班组里年龄最长的,却是整个团队的向心力所在。在他的时间里,是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和转业后十二年的采油工人生活。今年四十三岁的李荣辉,在油井和油井之间看到并追上了时间的脚步。李荣辉和他班组的时间,是他们在军旅生涯之外另一个战场上的保家卫国;在这个“战场”上,“拼命三郎”的他们攀登上一个又一个日产液量的“台阶”,创下了“风城速度”。
在风城油田两个班组之间,男人的时间和女人的时间,获得了统一。
晚上躺在风城油田作业区的宿舍里,想着昨天拾阶而上的黑油山。黑油山的传奇更是时间的传奇,时间让黑油山裸露冒油,冒出的油以时间的方式在行走。地下采油、地上旅游,“富得流油”是时间对克拉玛依的馈赠。黑油山是属于石油的时间,亿万年里它们沉睡,它们流动;亿万年它们一睡而过,醒来已换了人间;至此,属于石油的时间才刚刚开始: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运往各地。
黑油山下的克一号井,我把它当成时间博物馆,陈列着时间在克拉玛依的行迹,也是几代克拉玛依石油人奋斗的时间印记。他们唱着《克拉玛依之歌》走在采油的路上,走在炼油的路上,走在建造音乐博物馆的路上,走在设计“克拉玛依之歌”雕塑的思考中。在音乐和雕塑的时间里,容易让人忘记时间……
躺在房间,眼前柜子上摆着六瓶矿泉水。之所以注意到水,是因为走在克拉玛依的几天里,“水”和“石油”一样成了绕不过去的词。盛产石油的克拉玛依,却无比缺水。地下,本该储水的地方,流动的都是石油。
当年,作家汪曾祺蹲在伊犁河边感叹“自来新疆,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水对于人的生活的重要性”。以前在老家生活,后来在伊犁生活,我都不曾有这样的感觉。在克拉玛依的几天,我开始有这样的认识,所以每次下车时都要将没有喝完的矿泉水,带回房间接着喝。挖过井的人最懂得水的可贵,这是克拉玛依给我的另一种教诲。
缺水的克拉玛依,专门为水设立了一个节日,就叫“水节”,时间是每年的8月8日。从本世纪头年开始,已经举办了二十二届,一代人在水节的时间里长大成人。
近二十年前,还在老满城里上大学的我,从旧书摊购读过一本《共和国的血脉》,是一本写克拉玛依的长篇报告文学。厚厚的一大本,很快就让我陷入阅读的漩涡,对克拉玛依的印象虚虚实实,谜一样……我将原因归结为年轻。没想到,近二十年后,年届四十,才第一次走进当年从文字里进入的油城。时间呵,时间,还是没有解开我的一些谜团。
在克拉玛依期间,管住了自己的嘴,没贪杯。有闲时,翻几页《马桥词典》。以前没注意这是一本时间之书。韩少功在书中对时间的迷恋,对我理解克拉玛依也是一种启发。
走在克拉玛依,我一直被石油形成的时间之谜缠绕。在工业城市克拉玛依,诸多工业都围着石油做文章。这一切,对我都是新奇的。也就是说,我对这一切,都是无知的。直至走进位于独山子市的一个画家工作室,一幅幅作品,在画布之上,我看到了画笔的走动,更重要得是看到了时间,属于克拉玛依独有的时间在走动,就像埋在地底的石油管道,地下石油在流动,地上时间在走动。
时间之中又有时间,将我围在其中,克拉玛依成了进出时间的门。